我叫程舒琦。我想和你说说我的名字,我的话。
名字寄托着父母,甚至是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期望。我出生后,父亲取了很多个名字写在纸上让母亲挑,最后他们挑中了一个最中意的名字——程舒琦。随父姓程,“舒”意味着舒展、展示,也有希望我日后生活舒服之意。“琦”,与许多斜玉旁的字一样,意味着美玉。我的名字意味着“展示美玉”,父母认为,有一腔才气在胸是不够的,要学会展示和展现,表达自己。从小父亲就告诉我,不但要找到生命中的贵人,也要自己成为伯乐;不但自己要成为一匹千里马,自己也要有识人助人的能力和眼光。程、舒、琦这三个字合起来是三十六笔划,也有六六大顺之意。
我的名字跟父辈的名字很不同。我父母的名字,实在是当时年代最最常见的。父亲在1968年出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爷爷与奶奶都是工人。奶奶本想为他取名“红卫”,意为红卫兵,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去登记户口时,登户口的人悄声对奶奶说,把红卫兵作为名字,这怕是不太好吧,不如把“卫”改成“伟”,祖国伟大的“伟”!奶奶听了很高兴,细细思考了下,说,那就改成伟吧!于是,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红伟。母亲的名字同样充满着外公对祖国的一片热爱。外公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吃了不少苦头,后来通过自己的自学、努力和勤奋,当了干部。他永远有着强烈的报国情怀。他为舅舅取名“建国”,有建设祖国之意。母亲是他最小的孩子,他为她取名“建华”,意为建设中华。母亲也很争气,从小学习刻苦,考上了重点大学。舅舅在“建国”思想的指引下,成为了国家公务员。
细细思量,我的名字与父母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以及我现在的性格都很贴切。我开朗,爱表达,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熏陶下,我并不爱抢镜出风头,但需要我站出来展示自己时,我从来不胆怯扭捏,并且也乐于展现出自己的才艺和能力。我同情心重,爱助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帮助别人成长、发掘能力也使我感到快乐且满足。在人生的这18年里,父母从不给我过分压力压制我,而是尽他们所能让我站得更高,多看看这个世界,在童年让我尝试各种各样我想要尝试的东西:主持人、写作、花样游泳队、钢琴、吉他、舞蹈、书法……他们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自己去看去抉择,给我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在我做了决定之后全力支持我。我想,他们是以“舒琦”的标准去教育我培养我,而我也一直在朝着“舒琦”的方向成长着,以至于现在,我想再没有另外一个名字形容我比“舒琦”更贴切,也再没有一个名字能比它更适合我现在的价值观。不知是名字决定了人,还是人诠释了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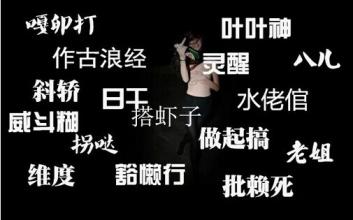 谈过了“程舒琦”,再谈谈“程舒琦”说的话吧。我出生在湖南常德,生长在湖南株洲,会说常德话和株洲话,虽然在常德只待到1岁左右就回到了株洲,但是一口常德话说得比株洲话溜上许多。不同的说话环境给人极为不同的感觉,紧紧接壤的长沙、株洲、湘潭的方言有着极为相似的发音,别说外地人,很多像我们这一代的本地人都分不清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方言像麻辣小龙虾和辣椒一样火辣辣的,说起话来仿佛一口槟榔在嘴里嚼着。也许沾染上湖南人骨子里原本就有的一股“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闯劲和一股匪气,这种方言听起来带着一种自信,以至于平时在学校上课、与老师同学交流都用“塑料普通话”(流传于湖南境内长沙、株洲、湘潭、郴州等地的普通话,因为带有乡音,所以我们习惯称为“塑普”)的我们,吵起架来都是爱用方言的,听起来有一种十足的自信与气场,以及对对手的不屑。而塑普,据我很多北方同学的观点,塑普听起来软软糯糯,和南方湿润的空气一样带着一股水乡的温柔。
谈过了“程舒琦”,再谈谈“程舒琦”说的话吧。我出生在湖南常德,生长在湖南株洲,会说常德话和株洲话,虽然在常德只待到1岁左右就回到了株洲,但是一口常德话说得比株洲话溜上许多。不同的说话环境给人极为不同的感觉,紧紧接壤的长沙、株洲、湘潭的方言有着极为相似的发音,别说外地人,很多像我们这一代的本地人都分不清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方言像麻辣小龙虾和辣椒一样火辣辣的,说起话来仿佛一口槟榔在嘴里嚼着。也许沾染上湖南人骨子里原本就有的一股“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闯劲和一股匪气,这种方言听起来带着一种自信,以至于平时在学校上课、与老师同学交流都用“塑料普通话”(流传于湖南境内长沙、株洲、湘潭、郴州等地的普通话,因为带有乡音,所以我们习惯称为“塑普”)的我们,吵起架来都是爱用方言的,听起来有一种十足的自信与气场,以及对对手的不屑。而塑普,据我很多北方同学的观点,塑普听起来软软糯糯,和南方湿润的空气一样带着一股水乡的温柔。
而我出生的地方——常德,这里的人说起话来仿佛在拉家常,音调婉转悠扬,常德比株洲更靠北,紧邻着洞庭湖,当之无愧的鱼米之乡,这里盛产莲藕、大米、牛肉,同样食辣但辣得湿润。如一碗常德牛肉米粉,白白韧韧清清爽爽,浇上鲜汤汁和切成小方块的五香牛肉,辣不在外表,味全在汤里,吸在米粉里。不像株洲那样一眼瞧上去菜盘子里都是红的绿的辣椒,常德话的辣藏在米粉白白的柔里,柔中自带一种韧劲。
出生18年后,我来到北京上大学。人在北京校园,耳边正儿八经的北京话其实少之又少,最多的是各色带着各地乡音的普通话。大家私底下评选最易洗脑方言:东北话、四川话、湖南话。只要你的宿舍有这么一位说这种方言的舍友,全宿舍就都被带成一种调调,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我东北的同学在我的“毒害”之下,说话满口湖南调调,别有一番风味。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南方海边,说话带点儿台湾腔的同学,在东北同学的“夹击”下,说着一口带东北味的台湾腔。方言成了我们日常谈笑的一大主题。
而在这些话中,除了从小到大说得最多的“塑普”之外,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海南普通话。海普的发音尤其像“塑普”,海南人大都幽默好玩,他们说起话来回转弯绕的调调颇有一种可爱,正如他们穿着沙滩裤,人字拖悠闲漫步海滩的率性。方言,是一乡人的脾性,是一乡人的态度,年年岁岁文化与历史,都藏在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