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2016年3月23日刊登了一篇报道《河南汝州爆发群体冲突? 官方:为避矛盾激化,即终止拆迁》。生活在当下的中国,只要瞥一眼标题,大家就能大体想象出来是怎样的拆迁场面,甚至连细节都可猜出一些。据《法制晚报》记者了解,2011年河南汝州市政府将温泉镇确定为汝州市唯一一个省级中心镇建设试点,并将土地卖给开发商,用以建设旅游产业开发项目。许多村民拿卖地分得的钱款盖了新房,但后期项目搁置。现在市政府又将曾经的试点区定义为棚户区,作为汝州市委、市政府2016年度重点棚改项目之一。于是要再次征收拆迁,3月10日全面启动棚改拆迁工作。但有的村民不愿搬走,于是3月22日下午部分村民与正在拆迁的工作人员爆发了冲突。从网络流传的视频来看,村民与上百位身着便装或制服、手持防暴盾牌的工作人员产生冲撞,多位村民向工作人员投掷石块,现场有老人受伤倒地,还有村民面部流血。中共汝州市委宣传部当日发表声明称:“为避免矛盾激化,棚改拆迁指挥部当即终止拆迁行动,撤离拆迁现场,第一时间安排专业医护人员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救治。”
幸福的拆迁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拆迁各有各的不幸。是非判断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这次拆迁悲喜剧,使我对“拆迁”一词又多咀嚼了一遍。
一? “拆迁”一词的今生和前世
对“拆迁”这个词的历史,我们没有做全面考察,但通过对词典中释义和用例的分析可以大体了解它的使用情况。
《现代汉语词典》一直到1996年版(修订版,后改称第3版)才收录了这个词:
【拆迁】拆除原有的建筑物,居民迁移到别处:~户丨限期~。(134页)
后来的两版(2002年、2005年)均未变化。2012年的第6版有了微调:
【拆迁】拆除原有的建筑物,原住户迁移到别处:~户丨动员~。(139页)
这两版的举例也挺有意思的,一是“限期拆迁”,不得商量;一是“动员拆迁”,劝君离开。词典编辑学家们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动员拆迁”和“限期拆迁”常常是等义表达,只有我们这些书呆子才想用语义分析的结果来规范现实行为。
其实,这个词并非1996年前后才出现。李达仁、李振杰、刘士勤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就收有这个词,且最早的用例时间是1984年:
【拆迁】拆除征用地段上的建筑物,迁走原有的住户或单位。例:①新住宅上马,需规划、审批、征地、拆迁,关卡重重,旷日持久。(《文汇报》1984.2.20-1)②实行这种办法,使拆迁工作化难为易。(《人民日报》1984.10.7-1)……(48页)
这似乎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但韩明安主编的《新词语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则将用例时间提前到1955年:
【拆迁】拆除房屋,迁出人口,多指国家为兴建工程在所征用的土地范围内把原有住户的房屋或其他建筑物拆除,使之迁往别处,由国家解决其迁居或迁建问题。△若按照这些规划进行建设,就要拆迁许多原有的住宅和铁路、飞机场、仓库等。(《解放日报》1955年11月24日)
比较这两部新词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关于“迁”的释义,会发现观察视角上的差别(或许也包含着时代内容的变化)。《现代汉语词典》中是“居民迁移到别处”或“原住户迁移到别处”,似乎是居民或原住户主动而为;而《汉语新词语词典》中是“迁走原有的住户或单位”,《新词语大辞典》中是“迁出人口”,对居民或原住户而言则是被迁。如果按当下各地拆迁办的做法,倒应该秉持这两部新词语词典的理解,当然,拆迁办工作人员最大的愿望倒是尽快出现《现代汉语词典》所设定的情景,这样拆迁工作就方便多了。

那么,“拆迁”一词是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呢?其实,根据“拆迁”本身设想出的可能的使用语境,或许应该有更早的使用。笔者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BCC)中就发现,最晚在清朝,就已经存在与现代意义相近的“拆迁”了。例如:
(1)给浙江仁和、海宁二县,修筑塘工,拆迁民房,挑废田地,价银五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有奇。(《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一百二十二》)
(2)国家设立城垣,原以保卫地方民生。凡靠城内外居民及瓮城内外居民,俱应听其安居贸易,毋庸拆迁。(清道光刻本《治浙成规》卷二)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拆迁”的主体都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单位、部门,拆迁的对象都是民房民众。
看来,拆迁是“古已有之”了。
二? “拆迁”的轰轰烈烈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拆迁之事,只要有政府主导的建设,它就有产生的可能。但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拆迁”一词,并不久远,往长里算大概也就三百来年的历史。如果房子和土地都是政府或政府可支配的,那么,拆迁之事就比较容易实施,“拆迁”一词就不会太火热。然而,如果民众坚守由自己支配的建筑物和田地的话,拆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尤其是农民想继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时候。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拆迁”成了一件大事,尤其是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遍地是拆迁,到处说拆迁,轰轰烈烈,盛况空前。在不同利益诉求主体的激烈博弈过程中,“拆迁”这个词负载了或者说浮现出更多的特殊色彩。从网络流传的一些2010年时任拆迁官员(现在大多已经落幕了,有的已成阶下囚)在面对拆迁问题时所发出的经典语录就可看出:
(3)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云南普洱市市委书记沈培平,2010年4月28日)
(4)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江西宜黄县政府一位署名慧昌的官员投书新世纪周刊财新网,2010年10月12日)
(5)跟政府作对就是恶。(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2010年10月14日)
(6)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2010年11月1日)
(7)现在全国关于拆迁都挺乱,你应该找人大探讨这个问题。……你应该报道高新区如何发展,应该报道老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应该报道老百姓如何不配合拆迁,影响回迁房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长春市高新区拆迁办调研员王洪义,2010年11月2日)
(8)不做市长,也要在20天内把梅龙镇铲平。(安徽省池州市市长方西屏,2010年11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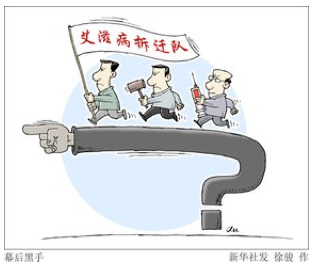
于是,出现“黑拆、血拆、艾滋拆”等各种“暴力拆迁”事件,就不难想象了。无需去查这些词背后的具体实例,一见到这样的组合,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散的黑恶气息。
这样的话说多了,这样的事做多了,一些特殊的气息就沾染到“拆迁”这个词上,人们一想起“拆迁”,就自然想起这样的场景,而且浮想联翩。
由此可见,拆迁≠拆+迁。虽然“拆迁”一词字面的意义是“拆而迁之”,然而某些拆迁工作者想达到的目的只有“拆”,而不管居民是否愿意“迁”,是否有处可“迁”,从而使“拆迁”浮现出新的景象,产生新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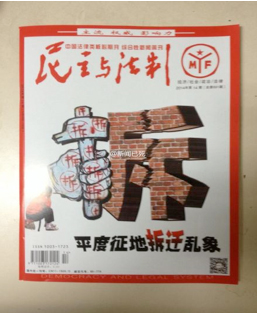
当然,有关“拆迁”所沾染的气息,远不止这些,丰富着呢,不及细说了。
这两三年,这种轰轰烈烈的拆迁乱象似乎少了一些,“拆迁”身上的特殊气息似乎也飘散了一些,但仍时有发生。当下的词语沾染的是当下的气息,而且有时某些气息会弥散很长一段时间。想当初,“小姐”一词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至今还没有完全洗却身上的特殊印记,就是这个道理。
三? 对“拆迁”的拆迁
词语,是时代的脉搏。
词语,是人际关系的记录仪。
词语,是有生命的,是在呼吸着的。
拆除“拆迁”身上的负担,迁移其特殊的色彩,大抵呈现出“拆迁≈拆+迁”时,也许就渐渐还原了拆迁的本色。
现实的事,不能靠词语分析来解决。但分析词语所处的生态,则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词语,理解生成词语、使用词语的人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