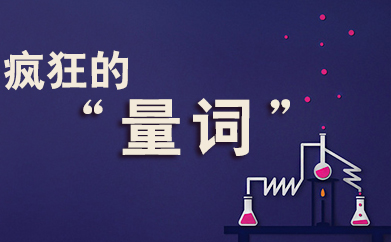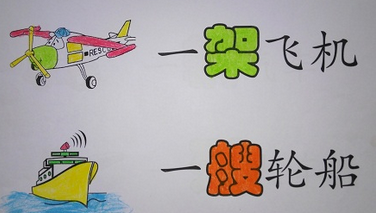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大量的个体量词如“个”“只”“头”“台”等等,用来表示具体事物的量,而英语、韩语或日语等语言中却没有个体量词,因此,个体量词的存在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一大难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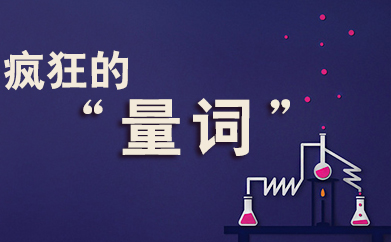 对于个体量词所做的本体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是,个体量词本身用得频繁而数量很少,极其复杂。特别是使用的“不定性”,这里所说的“不定”,是指各方言区中所使用的同一具体事物的个体量词并不相同,国内学生当然都能明白,也不会追问,而一旦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于个体量词所做的本体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是,个体量词本身用得频繁而数量很少,极其复杂。特别是使用的“不定性”,这里所说的“不定”,是指各方言区中所使用的同一具体事物的个体量词并不相同,国内学生当然都能明白,也不会追问,而一旦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一次我和几位朋友在公交车总站等车,当时下着雨,等得很着急,听到其中一辆车启动了,但是判断不出是不是我们要坐的那一辆,然后其中一位朋友就说“明明就是中间那张车在响”。我听了大吃一惊,“那张车”?这我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朋友是云南个旧人,她说,她们那里都这样说。后来,大家都聊起来,河南的朋友说,我们还说“一根裤子”呢,她解释的是因为北方冬天非常冷,放一条湿的裤子在阳台晾着,就跟冰棍儿似的,所以就有了“一根裤子”的说法。最近一次,朋友在韩国教汉语,问了我一个问题:“手机”到底用什么量词,她说韩国的教材写的是“个”,她本身是广州人,广州人可从来不说“一个手机”,而一般说“一部手机”。
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方言区量词跟普通话量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哪个才是标准的,还是还没有定论,只要不影响交际就可以。这关系到语言的地域性问题,其实也就是方言,方言代表着一定的当地文化,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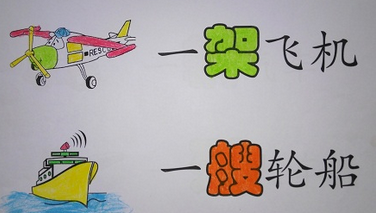 个体量词,似乎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化特性。拿粤方言来说,我们也通常说些跟普通话不一样的量词,比如“一辆车”,粤方言叫“一部车”;“一艘船”,粤方言叫“一驾船”或“一只船”;“一扇门”,粤方言叫“一栋门”;“一头猪”,粤方言叫“一只猪”;“一群人”,粤方言叫“一帮人”,等等。也就是说,量词跟其他像“儿化”(北方方言特色)一样,也是有其特有的文化色彩,地域色彩。而这样的地域文化色彩有时跟普通话中的量词相混用,或者普通话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应该是说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具体事物配什么样的名词,我相信已经有一部分是规定了的。但具体名词太多,而且形状、大小、使用功能等的具体事物难以有定论,比如“苹果”用“个”,“桃子”也用“个”,那么到底多大的东西,什么形状的东西用“个”呢?这是难以下定义的。而且新生事物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的不断出现,量词的搭配是否做到了与时俱进呢,这是一个问题。个体量词所存在的地域文化差异具体原因笔者暂时还未作很多的探究,但是,这不得不说对对外汉语教学造成了困难,对汉语学习者来说更是造成了困惑,尤其是方言和普通话相混淆的那些量词,比如说到底是“一部手机”还是“一个手机”或者“一台手机”,因为这三个量词对于北方方言区的人和非北方方言区的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在说话时造成心理紧张,也没有不理解和困惑,不像“一张车”那样奇怪。而有些北方方言区的人在粤方言区生活久了以后,有时也说“一部手机”。
个体量词,似乎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化特性。拿粤方言来说,我们也通常说些跟普通话不一样的量词,比如“一辆车”,粤方言叫“一部车”;“一艘船”,粤方言叫“一驾船”或“一只船”;“一扇门”,粤方言叫“一栋门”;“一头猪”,粤方言叫“一只猪”;“一群人”,粤方言叫“一帮人”,等等。也就是说,量词跟其他像“儿化”(北方方言特色)一样,也是有其特有的文化色彩,地域色彩。而这样的地域文化色彩有时跟普通话中的量词相混用,或者普通话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应该是说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具体事物配什么样的名词,我相信已经有一部分是规定了的。但具体名词太多,而且形状、大小、使用功能等的具体事物难以有定论,比如“苹果”用“个”,“桃子”也用“个”,那么到底多大的东西,什么形状的东西用“个”呢?这是难以下定义的。而且新生事物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的不断出现,量词的搭配是否做到了与时俱进呢,这是一个问题。个体量词所存在的地域文化差异具体原因笔者暂时还未作很多的探究,但是,这不得不说对对外汉语教学造成了困难,对汉语学习者来说更是造成了困惑,尤其是方言和普通话相混淆的那些量词,比如说到底是“一部手机”还是“一个手机”或者“一台手机”,因为这三个量词对于北方方言区的人和非北方方言区的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在说话时造成心理紧张,也没有不理解和困惑,不像“一张车”那样奇怪。而有些北方方言区的人在粤方言区生活久了以后,有时也说“一部手机”。
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个体量词的学习本来就是个难点,这样一来就难上加难了。因此个体量词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在本体研究中不可忽视,如果有必要区分普通话与方言量词的区别,那么就应该不遗余力地编制要具体到每一个具体名词的标准个体量词字典了。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毕竟这以后对对外汉语教学来说,也是有据可依的。